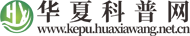
AUGUST 2023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人生的意义|乌尔善
我是七零年代出生的人,传统文化的教育大多来自小人书或者广播里听的评书。小人书一毛八、一两毛一本,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是一笔巨款,而且好久才出一本,一旦拥有就如获至宝,反复地看,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最顶级的小人书是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。我从小学美术,小人书看多来了,就在课本的边边角角、墙上画小人书里的画面,尤其喜欢画古装战争、骑马打仗,对古典神话世界有一种想象和向往。那时候,小孩们聚在一起拍洋画,谁拍起来就归谁,我经常照着画一张,《西游记》里的菩提祖师啊,《封神演义》里的太上老君啊,用水彩或者水粉画,等到天黑了,在昏黄的路灯底下跟人家玩的时候,混在真的洋画里去赢别人的,检验一下我画的是不是可以乱真,没有一次被人戳穿过。
2001年《指环王》上映,我看了很受震撼。我从小特别喜欢历史、神话和传统艺术,我能看到《指环王》里整个西方的文化体系,从宗教到历史、神话,包括西方古典艺术各个时期的元素,我都能够读解出来。我特别羡慕和嫉妒他们把他们的历史、神话和传统文化高度地集结在电影里,创造了一个这么恢弘的世界,我觉得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电影出现。
那时候,我也冒出了一个小小的念头:如果中国要拍这样的神话史诗电影,哪个题材适合?《西游记》特别有名,也有神话色彩,但不具备史诗的厚度;《三国演义》呢,有史诗的格局,但它不是神话的世界观;想来想去,唯一的题材就是《封神演义》,它既有真实历史的部分,又有一个特别庞大的神话体系,容纳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神话世界观,像盘古开天辟地、女娲抟土造人、三皇五帝这些,同时还有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、哪吒、杨戬这些民间的信仰,既有人类世界正邪之战,也有神仙斗法、妖孽横生,比《指环王》还要丰富精彩。如果让我拍一个神话史诗类型的电影,首选《封神演义》。
但在那一年,我还没有做电影,我想做一个艺术家。我大学考的中央美院油画系,二年级退学了,后来又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在此之前我没有关注过电影,当时电影学院广告导演专业第一次招生,我就考了。所以毕业后我做了十年的广告导演,拍广告为生,支撑自己做当代艺术,包括行为、装置、影像艺术,做一些展览,也拍展厅电影。
2007年,我决定重新规划我的事业方向,从当代艺术这种比较小众和个人化的创作,转向大众电影。之前我做的展厅电影只在电影节或者展厅里放映,我觉得,那不是电影真正的战场,电影的战场是影院的排期表。我想做在电影院上映的、观众买票一起去看的公众艺术,在主流的领域里去表达观念、传递美学、完成交流。展厅电影、当代艺术,我再老一点做也不迟,但现在,我可以先花大概二十年的时间去琢磨琢磨院线电影是怎么回事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,当代艺术创作全部停止,专攻电影。我选择了三个自己兴趣最集中的类型,一个是幻想类型,一个是动作类型,一个是史诗类型,未来十年到二十年,我希望在这三个类型里选择创作素材,做出主流的院线电影。
在我看来,拍电影不是青春饭,什么时候入行都不嫌晚。2011年,我39岁,我的第一部院线电影《刀见笑》上映,算是真正入行。在此之前,我是中国最成功的广告导演,但在电影行业,我是一个新人,那年我还拿了金马奖新导演奖。我当时说,新导演奖只能拿一次,但我希望永远做一个新导演,每一次都做新的、有挑战性的项目,去别人没有触碰的领域,这是我给自己确定的一个工作目标和工作态度。
2012年,我第一次尝试制作超级大片——《画皮Ⅱ》,打破了当时的华语电影票房纪录。我觉得,机会来了,现在我具备了市场号召力,也对幻想、动作和史诗类型的电影制作有了一定的经验,我希望启动“封神”项目。但我当时想从“封神”故事中挑一个片段,做哪吒的故事。2013年,我在做《寻龙决》,这部电影规模更大、复杂性更多,我的工作经验越来越成熟,整个团队的配合越来越默契,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做一个难度更高的项目。当时的中国电影对未来市场的预判也比较乐观,所以我重新考虑“封神”这个项目的时候,还是想完整地讲这个故事,于是重新做了规划,让助手缩写《封神演义》100回的章回体小说,我们讨论了故事结构,决定用三部电影来完整呈现。《封神三部曲》项目在2014年6月正式启动,我的第一个儿子也在那时候出生,他就成了这个项目的坐标。只要看到他,我就特别具象地看到这个项目所经历的时间。现在他9岁了。
我做事的态度是:做最坏的打算,尽最大的努力。如果你想好一件事的代价,认为自己可以承受,那就不用犹豫。《封神三部曲》项目周期长,风险也比较大,我在一开始就想到了最坏的可能。一是可能拍不完,因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没有这么大的投资,没有三部连拍,而且八到十年后才能上映,意味着这几年我没有其他的工作。二是不知道票房会怎样,我之前的电影,无论商业票房还是作品质量方面都没有败绩,资本非常相信我,但是下一部的票房是很难预判的。
对电影来说,观众和资本都是你的伙伴。资本的信任是很宝贵的,一个职业导演也要对投资方负责。投资方投入了大量的资本,我投入生命里最宝贵的十年的创作黄金期,彼此都投入了最宝贵的资源,竭尽全力去做这个项目。之前十年的信誉,我得到了这个机会,未来十年的努力,我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目标。如果成功,大家都满意,如果失败,无非就是用十年去补偿呗。我跟太太商量:最坏的结果我们可不可以承受?太太说,没问题,你去做吧。接下来这十年,就拼了。
这个项目要工作八到十年,我也为此做了一些生活上的安排。我们要在青岛拍摄将近两年,这期间我很少能回北京,我的父母亲都八十多岁了,所以我请他们搬到我住的小区,这样我太太好照顾他们。然后,我去做了一次全身体检,结果显示,我的健康状况支撑十年不成问题。做完这些,我安心地启程去青岛了。
选择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项目是不容易的。一个导演的创作周期是有限的,因为导演工作的体能消耗非常大,所以要做一个规划,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题材、项目。我觉得,壮年时期适合做制作难度大、挑战性强、工作强度大的项目,在体能下降的阶段适合创作思想更深入、更尖锐的项目。出于这样的考虑,在四十岁左右,我选择了《封神三部曲》。
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,一个民族从经济繁荣走向文化自觉的时候,也应该出现这样的电影。当基础生活的需求满足了之后,人们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感兴趣,追溯民族文化的根源,追问“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”。这样的电影,就算我不做,可能也会有其他导演去做,正好,我赶上了这个时机,那我就做吧。
到现在,我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,让我这十年过得非常充实。十年看起来长,其实我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。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创造性地去解决,集结之前从来没有被集结过的创作资源,探讨出便利高效的工作方法,工作量非常庞大,难度超乎想象,再加上疫情,但我们最终顺利并且安全地完成了三部电影的拍摄。
拍神话史诗电影,一个巨大的难题是核心创作资源的组织。当时我们国内拥有的创作资源还不足以支持我们项目的难度,从剧本创作的角度,之前没有神话史诗作品,完全是拓荒;从制作层面,它触及到整个电影工业上最高难度的类型——神话史诗,要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,这远远超过我们当时的制作能力。以视觉效果技术为例,封神的故事里有大量的异兽角色,比如雷震子、麒麟、龙须虎,但是数字生命角色是当时中国电脑视效的盲区,当时只能做数字场景、数字道具、非生命体。为此,我们成立了一家视效公司魅思映像,中国艺术家和国际最好的电子艺术家合作,专门服务于《封神三部曲》,电影里大量的老百姓、千军万马冲锋、成千上万劳工建造祭天台,全部是数字制作。我们要拍古代骑兵战争,但是之前的中国电影里马术组是非常薄弱的,只限于骑在马背上走一走,没有形象漂亮又能完成复杂技术动作的马匹,怎么办?我们从买马开始,然后请世界顶级的马术指导和团队来到中国跟我们一起训练马匹。
另一大难题是制作规模带来的管理难度。要做一个突破文化壁垒、全世界观众可以看懂的史诗级神话,我们的很多创作部门邀请了国际顶级的创作者加入,整个剧组里有来自二十个国家的工作人员,先后进组的登记在册的工作人员超过8000人。我们的整个制作流程采用了国际通用流程,各方面的标准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流的。
我最怕听人说“这好办”,这是我判断主创的一个基本原则。你认为一个项目有难度,说明你客观地评估过,但凡说“没问题,这事容易”,基本就是有问题,可能你没想清楚,轻视了工作中的难度。我不怕听人说“好难呐”,我会说,你认为难在哪里?只要你想到的,我们一起讨论,总能找到解决的方法。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,只有没有想到的问题。
难度多大,成就感就有多大。工作越有难度,我越有兴趣。一件很难的事情,我们攻克各种困难之后做到了,会带来很大的快乐。做一个电影项目,无非也是消耗自己生命中的时光,无论怎样,生命都会被浪费掉,何不找一个有挑战性的项目去浪费呢,何不把生命消耗在有意义的事情上。
我有一个工作方法,把情感力量作为一颗种子,去找到创作的动力。小说《封神演义》是明朝人带着明朝的世界观、价值观虚构的一个上古神话故事。我们重新讲述的时候,要用现在的价值观、世界观和情感体验重新去认识、判断、筛选,这个故事里哪些东西触碰到我们的内心情感。我看了大量的素材、资料、背景知识,看完之后问自己:如果没有视觉效果,没有电脑特技,没有神仙大战,还有什么可以打动你?如果你只拿到很少的投资,你还愿不愿意拍这个故事?这个故事里哪一个人物、哪一个事件深深打动你,让你念念不忘?
找到了关键的两组父子关系之后,我确定我能做好这个故事。《封神演义》中对我情感冲击最强的事件,就是姬昌吃了伯邑考的肉做的肉饼,逃回西岐,带着巨大的沉痛,吐出了三只小兔子。一个父亲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痛苦和屈辱?商王殷寿为什么要做这么残忍的事情?这个事件对姬昌、姬发父子和这个家庭有什么样的冲击?可以说,这个事件是整个故事的核心,它决定了周一定要灭商,决定了武王必须伐纣。还有另外一组父子关系也非常耐人寻味,就是殷郊和殷寿。殷郊原本很爱父亲,但他父亲要把他斩首,殷郊在斩首台被神仙救走,获得了法术,准备回来付向父亲复仇,但是,最终他还是站在了父亲那一边。这个儿子非常矛盾,他对父亲的爱和恨都很强烈,比哈姆雷特还要复杂。
如果没有制作成本,没有电脑特效,没有那些包装手段和娱乐性的效果,我也愿意拍这两组父子关系和两个家庭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真的值得讲给全世界的观众,它强烈地打动我,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打动别人。故事中的情感可以跨越时代、跨越民族、跨越文化背景,它是建立在每个人体内的、穿透所有人普遍经验的情感。我很有愿望去做这个表达,有了这个动力,我坚持工作十年没有问题。我不可能十年为了票房数字去工作,为了漂亮的视效去工作,那些无法支撑一个人真正全心投入地去工作。
神话是什么?神话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?神话不等于历史,《封神演义》不是商周的历史还原。神话是民族精神的隐喻式表达,一个故事历经千年,不断地成为一代代的父母讲给孩子的故事,是因为这个故事触及到一些世界观和核心价值的表达,以及根本不变的生命的智慧。它是一种隐喻,它是一种象征,它是一幅通往心灵的寻宝图。
一个神话史诗,核心往往是善恶的对决。在我们的故事里,姬发一开始崇拜殷寿,把殷寿当作精神上的父亲,蔑视自己伦理上的父亲。随着剧情发展,他发现了殷寿的虚伪和邪恶,发现了父亲姬昌看似脆弱但是内心非常坚定的善良、正义和真实,最终姬发也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和可以相信的价值观。这是全人类对真相的追求、对“什么是善”的追问,这种观念是亘古至今始终不变的,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去获取营养、坚定信念的宝贵财富。我们应该重新去表达,把它变成一个当代观众愿意听、愿意看、愿意在一个轻松的娱乐化场景里感受的故事。
电影的魅力在于,它能够创造一种丰富的体验,既有感官的娱乐,也有情感的交流,还有思想的碰撞,又有美学上的建构和展示,和观众形成多层次的沟通。我喜欢的、理想中的电影是这样的,这也是我做电影的目标。我放弃了小众的艺术创作,转而成为院线电影导演,最重要的动力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些这样的电影,不因为娱乐性强而肤浅,也不因为思想深刻而晦涩,能够平衡几个层面的需求,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。
我从小就听老师说:乌尔善,你就是一匹野马。我小时候很淘气,不听话,上课时交头接耳、接话茬,老师们无法控制我,经常把我请出教室去。但我学习特别好,小学毕业是全校第一。上中学时,我开始对蒙古族的历史感兴趣,知道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从何而来。
乌尔善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“前进”。这些年来,我的每一部电影作品和上一部相比都是一个进步,从规模、资金到故事背后的文化体系都丰富了很多,我一直在向前进。我的兴趣和我的工作高度重合,我喜欢文学、戏剧、美术、音乐、历史、心理学,拍电影能充分地把我所有的爱好集中在一起。每次拍电影,我都会找到自己最想研究的事情,比如拍《封神三部曲》的时候,我去研究神话学、历史,去琢磨电脑视效方面的新技术;为了训练年轻演员,我自己先去上了三个月的表演课,再给年轻演员们设计表演课程,跟他们一起排练,这都是我特别有乐趣的事情。也许,每一次你把全部的热情和快乐、全部的生命的能量都放在一件事情上,更容易产生一个好结果吧。
摄影王海森
采访、撰文Maggie
统筹暖小团
化妆、发型Shailen、吕敏
造型傲寒
美术编辑孙毅
助理 润迪
场地鸣谢南洋文创园
新媒体编辑Sissi Hua
排版新月